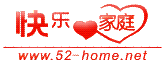卫生行政的“朝”与“野”
卫生行政,是卫生知识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然而,长久以来占据国人医疗生活主体的中医为什么没有获得这种行政权力,却拱手让于西方医学和卫生学呢?或者说,公共卫生制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内产生?这是一个类似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李约瑟式难题。
喜卫生而厌污秽,本是人之常情,传统社会并不缺乏提倡卫生的记载,对卫生与防疫的关系也是有所认识的。若《周礼》一书可靠的话,周代政府就有负责清洁卫生的官职,负责宫廷内外的除草、除虫以及清洁水源的工作。宋代《梦梁录》载南宋临安“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但是这些行为,都没有上升成为全面的公共卫生政策。这与传统医学的病因观是有关系的。
传统医学将疾病的主因责之于“天”,为四时之气不正所致。天之四时无从控制,气又是无形无质无从把握,因此,欲健身防病则只能从增强人体正气着手了,此即所谓“养生”。中国古代很少用“卫生”一词,即使出现也往往与“养生”同义。养生主要是针对个体的行为,其原则包括增强正气和远避邪气。后者就会造成一种伦理困境,在南宋时候就已经引起争论——有人染疫时,其家属可否以避免传染为由弃之而去?大儒朱熹参与了这一讨论,他反对有些人否认疾病会传染的事实,认为:“予尝以为诬之以无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虽有染而不当避也。”他的方案是倡导“恩义”,使人们“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用道德勇气来对抗疾病。
参照近代的知识,真正解决这一伦理困境必须依赖于有效的技术。朱熹说疾病“染与不染亦系乎人心之邪正、气体之虚实,不可一概论也”,但由于传统的“疫气”观很难说清楚疾病传染的道理,因而不能消除恐惧。提倡养生以增强抗病力,或焚烧香料或香药来驱逐秽浊之气,这些方法行之一身或一室不为无效,但不能成为规范行为的基础。官府不可能规定每个人必须强身以及如何强身等。而近代的“卫生”,基于微生物传染疾病的生物性认识,发展出一套阻断传染的技术手段。例如清末颁布的《预防时疫清洁规则》这样规定:“沟眼发生臭味时,须以绿汽灰、松脂渗入之或石灰消除之。”“当开沟时须先用绿汽灰、松脂或石灰令辟毒臭。”广东巡警道于1909年发出的鼠疫防疫告示则有这样的指引:“屋内宜勤加扫除,并宜常用几阿连水(即臭水)洒地,墙壁旧者用石灰水刷洒,床脚、沟渠、厕所等处,均宜洒以石灰粉。”“此病之毒,易由伤口传入。各宜随时留意,不可使身有伤口。设有之,须注意解毒法。其法以二十分之一石碳酸水洗患处(石碳酸水即加布力水。此水制法,石灰酸五分,盐酸一分,水九十四分)。洗后用洋来合口膏贴之(即俗称孖指膏)。足有伤口,尤不可徙跣而行。”这些来自西医的技术,使预防传染有章可循,成为制度。甚至可以建立专业化的护病机构,通过托管来解除亲属护病的危险。由于这些技术操作性强,即使对民众习惯的某些 “私权”带来侵犯,亦能以多数人利益为由来强制实行。
因此,近代政治中的卫生事务绝非基于个人自主选择的私事,而是凭借社会和国家的力量来强制实施的公共事务。从个人而言,中医的养生本来是一种长久而便利的根本方法,即使在今天仍然有提倡推行的必要。只是从公共性而言,西医的技术特点使其更易于推行,因而把握了行政话语权。所以,清末除太医院仍以中医为主外,一些新设置的医官职位都已交给了西医。
由于传统政治缺乏医疗卫生方面的系统管理,可以说中医本就算不上“在朝”,到近代由于西医开始占据卫生行政权力,却一下变成了“在野”。西医有卫生学方面的长处其实并不意味着全面的学术优势,但因为与行政权力的结合而影响力陡然增大。在清末,西医的“在朝”还局限于卫生防疫等领域,然而这仅仅是个开端。广义上的卫生行政,还包括医生执业、注册等管理,如果这些权力顺势为西医所掌握,加上立场不客观不公正的话,那么中医就不免要面临一场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