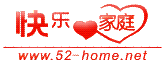那年,在国家图书馆,我聆听了文坛名宿文怀沙老先生的诗词讲座。你看他,银髯飘拂。出口成章,妙语联珠,思维敏捷,对事业、对朋友、对生活充满了热情,难怪各地的诗人才子为之倾慕,接踵叩门讨教。
文老何以能这样越活越年轻呢? 这与他幽默豁达的性格和坦荡的生活态度是分不开的。 文老分析自己的心理活动时,借用道家的“委心任运”加以概括。即听任心灵自由驰骋,不为名缰利索、荣辱得失所左右。可谓忙而不计利,勇犹忘险。
文老自谦“离休在家,述而不作”。可如果你以为他“年高耄矣、无所为矣”那就错了。实际上文老活跃得很,不久前,他还应邀录制了吟唱毛主席诗词的录音带呢。
文老的古典文学造诣颇深,28岁即为教授。在旧中国,他公开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写文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老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仍知无不言。他见到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现末句的“发人深醒”的“醒”字,应为“省”字笔误。他心想,日理万机的领袖偶尔疏忽是难免的,可悲的是全国报刊如实照登,没人敢说这是个错别字。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文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众宣称:“只闻沉睡.不闻深醒,人如深潜梦底就醒不过来了。”于是被斥为奇谈怪论,科以“攻击”罪,冠以怙恶不悛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文老一生坎坷多难,衔冤负重,但他活得轻松洒脱,不仅善于苦中求乐,而且有一种更高明的心理转化法,或称心灵辩术。1970年,他在山西狱中,肝疼剧烈,头上直冒冷汗,经狱医确诊为肝癌。旁人都替他捏把汗,他却不时高兴得大笑,人们都怀疑他神经错乱了。其实这时,他脑子非常清楚,悟出了一个道理:痛苦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可省略的表现形式。人在经受、领略痛苦的同时也在经受和领略生命的存在。这是热爱生命者以苦为乐的根据。奇怪的是文老自从跳出狭之缓解了。
打倒“四人帮”后,文老从狱中出来。已无家可归,只好暂借两间房栖身。在这个新家里既没有他昔日当教授治学的藏书,又无豪华陈设。在屏风隔开兼作卧室和书房的小屋墙上,挂着“斯是陋室”四个毛笔字颇具雅趣。从中不难体会他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情怀!他还幽默地说:“人死后不要搞遗体告别,再隆重本人也不知道了。我希望我一旦生命垂危,能召唤朋友来到身边,亲聆褒贬之声,这样的告别仪式岂不有意义得多。” 一次,电台编辑播放文老吟咏的诗词之前,怀着沉重、怀念、敬佩的心情告诉听众,这是著名吟咏大师文怀沙先生的遗作……文老在上海的兄长听到后,慌忙跑到电台去询问,当即打电话到北京,而文老听说后,快乐得彻夜未眠,他说这种“死”的体验太美好了.并连夜给电台的编辑写信,没有丝毫贵怪,真诚地感谢他们让他活着听到了身后的赞誉。
文怀沙老人如此豁达健康,问其养生之道,文老说:“万变不离其宗,锻炼是健康的重要保证。”年轻时,文老就酷爱体育锻炼,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五届运动会.获得跳高比赛第五名,成绩是1.74米,正好跳过自己的身高。按今天的标准,当时的文怀沙可以进国家田径队,起码也算是运动健将了。在监狱接受改造的那些年,身体状况极差的文怀沙找到了特珠的锻炼方法—扫街。拿着笤帚,从东到西,由南至北,扫得认真仔细,扫得通身大汗,不但活动了身体,还因为表现好受到“表扬”,少受了些皮肉之苦。如今文老还经常散步。他认为,老年人锻炼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过量,否则,不仅达不到锻炼目的,甚至会适得其反.真正成了“垂死挣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