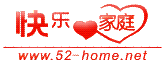那一段时间,我无休无止地看着碟片,像一只黯然神伤的蜗牛,缩在北京一个几平方米的小屋里,等着毕业,等着9月的来临。佑安的信,则安静地躺在一旁,一遍遍地,被我看皱了。
佑安在信里说:蓝,记不记得我们刚刚相识的时候,曾经因为争抢着要看同一张碟片,而在校门口的音像小店前,互抛白眼,彼此怨恨?那时的我们,多么的年轻,眼白里抛出来的忿懑,都是带了透明的露珠的。
你说那张碟片,是你预订了许久的。我便说,许久有多久呢,看你的校徽,就知道你也不过是和我一样,入学才两个星期吧。你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最终将手中的碟片一甩,扭头走了。
而我,却是突然奇怪地追上你,又将你一把拉住,笑着央求道:好姐姐,求你别哭了,我先让给你看还不成吗?蓝,我在你的笑里,看到了自己,那样纯美透明的青春,像一只刚刚褪去外壳的彩蝶,终于新鲜地探出头来,开始飞翔……
我很想告诉佑安,我当然记得,我们一同走过的每一丝痕迹,我都细细收藏进我的行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他们划掉。可是,佑安,你一直这样走,走到我再也看不见的风景里去,是不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我们所有的情谊,只能活在记忆之中?是不是即便时光倒流,那一段流光溢彩的影像岁月,也无法完好无损?就像,这一场毕业,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