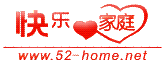四
我做记者十年,才正学着从常常会有的道德评判和政治正确中尽力脱身,去试图观察,只是观察。
但赵铁林压根连这个姿态都没有。
“我和她们交往,拍她们,并且告诉她们我的目的,这对她们来说就是对她们的尊重,她们知道我不会扭曲她们。”
有学界的人说他的照片是“参与式观察”
他说:“参与没错,但不是观察,是和被拍摄的对象共同处于边缘的生活状态。“
五
当年他给过我一张名片,名字上有一个黑框。别人问,他就笑“我死过很多次了”
他说“生死寻常之事”。
我们后来再没有联系,一直到前天朋友说起,才知道他一年前已经去世,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出生在战场上,被寄养在乡下,在文革中母亲自杀,他去矿山挖矿,六十年中他一直颠沛流离,临终前住着45平米的房子,骑着自行车来去,他遇上了中国纪实摄影的“也许是最好的时代”,他也知道选择这条路就是“选择了贫困”,但他选择了。
我在网上看到他去世前的照片,看到他被折磨的样子,心里不能平静。
但写下这篇文章,并非要唏嘘他的命运。
他象他拍摄的人一样,承受命运施加于身的一切,并不粉饰和夸张,也不需要怜悯或者虚浮的敬意。
十年前在那篇文章里,我写过他的照片向我揭示的真理: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我们将浑然难分,象水溶于水中。”
文章来源(柴静_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