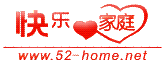千岩滴透原无色,
一线穿空若有声。
信是当风吴道子,
古灯如月我高擎。
一部《范曾诗稿》,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对于古风、绝句、律诗、对联、曲等不同体式的准确把握和娴熟运用。在表达不同的情致、不同题材时可以选择相应的体式和韵字。对于律诗,范曾先生素所青睐,曾有贺杜甫《秋兴八首》发表。他以为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格律最严谨、形式最完备的体例。而先生信奉在严格的规矩中,大手笔往往能拓出奇境。倘不是对于古典诗歌语言把握到这样的程度,那对于这一古老形式的任何贬损和顶礼都可以视为一种迷信。是不足为训的。
《论白描》内容固然写了对绘画中白描的感悟,而诗歌的妙处,也正在于若即若离的语言技巧。感觉、视觉和听觉,眼前、过往和将来,都说到了,可又都没有着实,是可视的线条吗?分明又是一种天籁之音。这些纷纭变幻的感受,既是读者人人心中有而笔下无的存在,又是具备深刻实践感受的艺术家个人的高峰体验,诗的奥妙尽在这种难以明言之地。